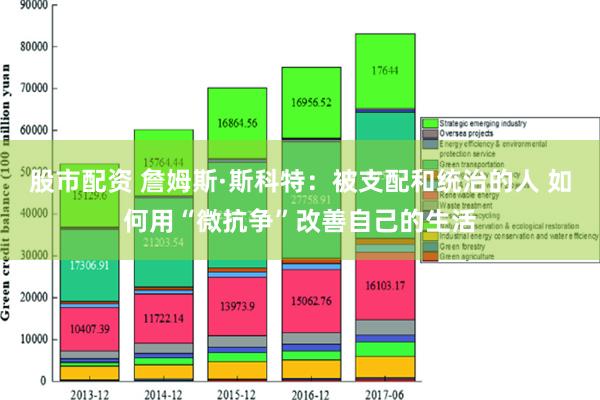
[ 反抗的的确确存在着,就在人们的心领神会里,在人们自发的行动和口头所说的一系列词汇里,他们开小差、搞破坏,他们在土地上一蹲好久,以此来表达不满。没有拼个鱼死网破,而是想方设法地活下去——这种心理听起来绝对合理,避开最严重的伤害和压迫致死,是明智的抉择。 ]
打字员给一位学者打好了他的书稿。书要出版了,照例,学者得写个“前言”来感谢所有与书稿有关的人,例如导师的提携,行业前辈的关照,配偶儿女的支持。这位学者很周到,首先没有忘记感谢一下打字员,他写道:
“简妮·米特纳赫特(打字员的名字)为我做了许多工作,不限于打文稿,还修复了我因早年忽视语法和拼字比赛而导致的大量损害。”
“破坏”的原文是“damage”。在这本书的中译文中,译者将其译为“文字硬伤”,固然是准确的,不过欠缺了幽默感。要知道,那种“讲真”式的幽默可是此位学者最大的特色之一,且总是在写前言的时候露一峥嵘。他接着说:我的妻子儿女,讲真,我不感谢他们对我写书的支持——他们根本不感兴趣,反而总是把我拉回到家庭生活里去(但愿他们能一直这样)。他又说:
“讲真,我不想按惯例,说什么‘我要为本书的错误包揽全部责任’‘所有错误与他人无关’了。因为我写这本书,显然从这么多的学者那里学到了这么多的东西。所以我这本书,是集体参与的成果。如果事实表明我这条路走错了,那么我想,这么多的学者跟我一样,都坐在同一辆错误的车上。”
这位爱“讲真”的学者是詹姆斯·C.斯科特,1976年,他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》,在前言里就以如此的率真,把学术写作的正确套路一一打破。好读人文书的人都会有个印象:人类学家最幽默,最善于放下架子讲真话,斯科特就是一位从人类学起步的学者,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》是他在缅甸和越南两地的田野考察后的成果,对他来说,诚实的人理应毫不犹豫地对自己选择的“事业”表达怀疑,厌烦乃至憎恨写书,是一个以写书为立身之本和进身之道的人的正常反应;尤其人类学者,深入一片土地后见识到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,产生苦辛甜怒,相比于这些,写书,而且是按着经过训练的规范去写书,去寻求资助,申请出版,这些事终归是太乏味了。
1998年,斯科特出版了《国家的视角》一书,主题挺“刺激”,考察了20世纪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,在发展中采取“社会工程”后遭遇的失败,比如苏联的农业集体化、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农村改革、巴西的现代城市建设等,都是他研究的案例。他依据自己养蜂的经验,用蜂房设计的革新作类比,说现代国家机器运行的基本特征,就是对真实的社会生活做“简化”,设计出的制度便于对人民做统计、摆布和控制。在给此书写前言时,斯科特又在结尾时开始“说真话”:
“我希望踢开写书的习惯,至少有一段时间这样。如果有类似戒毒所或戒鸦片一样可以治愈写书瘾的地方,我一定会接受治疗。我的习惯已经花费了我许多的宝贵时间。写书和其他的瘾一样,戒除的时候很伟大,但一旦痛苦缓解,瘾头很快又会上来……”
虽然有写书的瘾,可是斯科特对书的要求是相当高的,从1976年到2024年7月19日离世,斯科特的著作一共还不到十部。当然,每一本都是掷地有声,甚至可以说大多有“破圈”的效果。破圈,就必须有一些一看就很刺激的主题,就以大名鼎鼎的米歇尔·福柯为例:福柯赖以“破圈”的著作是《疯癫与文明》《规训与惩罚》《性史》等数本从题目上看就很具公共吸引力的书,监狱、疯癫、性、临床医学之类,易于使最大多数的人产生兴趣。斯科特的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》,似乎是一个很“偏门”的题目——人们为什么要关心缅甸和越南的农民呢?他们用不用得上联合收割机,他们遭遇现代化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苦乐,有哪点能击中广大英语读者的兴趣点呢?
简单的回答是:斯科特的关注点是“反抗”。
反抗与生存
说起反抗,就会联想到流血冲突,联想到挥舞的拳头,革命旗帜与遍地火海的战争。而在建立了民主制的西方国家,反抗的概念则与游行示威、党派政治联系在一起。但是斯科特在耶鲁读研的时候,去往了越战期间的越南,对那里的农村社会有了兴趣。有的农民占有更多土地,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,他们之间是不是理应存在“阶级斗争”?是否应该有压迫、有反抗?但斯科特发现那里真实存在的,是另一种潜隐的、地下的斗争,表现为怨恨、愤怒、诽谤、暗中破坏等。越南农民对机械化的到来充满恐惧和敌意,他们通过言行、心理来表达抵触情绪。
这些绝非明面上的阶级斗争或是革命之类。农民们的斗争,其手段是受限的:他们没有请愿,没有示威游行,也没有暴动。所有相关理论总结出来的东西,对他们都不适用。可是反抗又的的确确存在着,就在人们的心领神会里,在人们自发的行动和口头所说的一系列词汇里,他们开小差、搞破坏,他们在土地上一蹲好久,以此来表达不满。没有拼个鱼死网破,而是想方设法地活下去——这种心理听起来绝对合理,避开最严重的伤害和压迫致死,是明智的抉择。
斯科特没有在大多数人不会感兴趣的地方信息上费笔墨,例如,没有拿这个村那个村的名字来烦扰读者,相反,他通过越南和缅甸农民的案例,大胆探究了一个看起来新鲜却更加符合人们感知的现象:多数时代,世上的多数地方,都并没有革命,动枪动炮的标准版“阶级斗争”是罕见的,只是存在着紧张的阶级关系,在其中,农民没有结党,没有可以赖以直接“干一票大的”的武器弹药,他们为了活下去而采用的策略,是通过设计一系列其他方法来应对压迫和剥夺,以尽量减少自己所面临的损失。
被无力感控制的人,或是依附他人生存的人,他们的行为抉择,成为斯科特一生中最专注的主题之一。他关注越战中的逃兵,关注饥荒中的偷窃,他去搜罗那些监狱里的人写下的东西,去捕捉他们的声音,它们都是他所说的“潜隐文本”,是只有通过深入那些人的日常交流,深入他们的语言,才有可能接触到的。他知道,那些英语流利、能说会道的人,一般都是那些地方的精英,他们同一个田野考察者讲的话,与他们聚在一起时彼此会说的话,哪怕是同一主题,内容、音调也是完全不同的。
相通的体验与地方性知识
在耶鲁大学,斯科特曾在课堂里发起过一次尝试:他要学生们用25分钟的时间,写下自己曾有过的最深刻的无力和依赖他人的体验,写下它们的后续——这种体验是如何发展的,感受怎样,日后是否解决。这些学生都有不错的家境,没受过真正的生存之苦,他们写下的内容,一大半都是关于单恋:恋上某人令他或她沉溺在依赖和无力感之中,取悦别人,渴望变成对方喜欢的样子,结果一般都是失败。在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》里,读者会发现,东南亚农民的心理是如此真实可感,那种想要变得“更好”又不得不承认做不到,深深依赖他人,同时不断埋怨他人、中伤他人,以此来谋求被对方注意到的“反抗”,竟然跟自己的体验十分相通。
1975~1976年是新史学、口述史兴起的里程碑时期。斯科特写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》时,曾在法国很深入地研读了年鉴派,勒华拉杜里的划时代之作、研究12~13世纪一个法国村庄的《蒙塔尤》,就是1975年问世的。此外,那两年由专业历史学家出版的破圈名作,我们还可以说出像是《万历十五年》(黄仁宇著)、《王氏之死》(史景迁著)等大名。
和这些书相似,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》用大量地道的学术语言勾勒画面,讲出许多被忽略,同时又极具人文主义的普遍意义的“地方性知识”。像是说到地主和佃户,这一组理应归于“统治—依附”“压迫—反抗”的关系时,斯科特勾勒出一幅细致非凡的图景,例如,在说到湄公河三角洲(越南的交趾支那)的那些年老的地主如何怀念旧时的日子时,他写道:
“那时候,作为对佃户服从的报答,他们帮助佃户应付生老病死等大事,佃户如有需要他们便提供贷款。但我们不能夸大地主的慷慨,他们一开始无疑是投机者。也许布罗谢诺的结论是正确的:‘像救治病人的医生有时免费分发药品一样,由于歉收而减租的地主,以及收养佃户子女的地主,也不算少见。’当然了,说仁慈的地主‘不算少见’,也暗示了仁慈的地主并不是典型的。”
单是这样一段分析,就足以使读者懂得,一个合格的人类学者要具备怎样的耐心,写一本好书又是多么的不容易。斯科特对地主(标准的统治者和压迫者)的描述,固然颠覆了一般人的想象,然而,在展示他们的“慷慨”“仁慈”时,斯科特又及时地加以限定:慷慨是存在的,但不能夸大,仁慈是有的,但并非典型。颠覆成见没问题,但下一个简单的小结论,这种事,斯科特是绝不会做的。
亚特兰大联储总裁波斯提克(Raphael Bostic)表示,他期望在今年第四季开始缩减购债规模,但如果就业市场持续强劲复苏,他也愿意提前实施。他指出,长期利率正在上升,他认为如果未来一两个月的数据如此强劲,那么美联储的目标就会取得实质性进展。他也同时强调,强劲的市场运作意味着,可以实现相对快速的资产购买缩减。这显示出,波斯提克与里奇联储总裁巴金(Thomas Barkin)都认为,通胀已经达到美联储设定的2%门槛。
为了字句之间的严谨,作者付出了如此的苦心,还无法期待读者们给予留意。斯科特在晚年的一次口述采访里说:没有不好的宣传,哪怕是完全歪曲我的观点的宣传,都是好的。写书就像养孩子,养大之后,把他送出门,让他在世上自己闯出一片天,无论他遇到什么,无论别人怎么误读他,怎么轻率地使用他所包含的术语、概念和理论,作者都不会再去修改自己培养成品的孩子——他的书了。细读过他的书,就能理解,那些用“讲真”来自嘲、来开玩笑的前言,是他写完一本书后真正松弛下来的证明。
无政府主义者眼中的世界史
无论怎样严谨,也必须从一开始就注意可读性。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》的开头,斯科特引了一位学者R.H.托尼的话:“有些地区的农民……像一个水没到脖子的人,一片涟漪打来就会淹没他”,用这种具有画面感的“插曲”开启一本书,是斯科特一直坚持的一种写作策略。在1998年出版的《国家的视角》里,斯科特讲了一个与1765~1800年间的德国林业改革有关的故事,我摘其中的一小段:
“有价值的植物是‘庄稼’,与它们竞争的则被贬为‘杂草’,吃它们的昆虫被贬为‘害虫’。树有价值,因为出产‘木材’,而与它们竞争的则是‘杂’树,或者‘矮树丛’。对动物也采取同样的逻辑。具有很高价值的动物是‘狩猎的猎物’或‘家畜’,与它们竞争的、猎食它们的动物则被归为‘食肉动物’或‘害兽’。”
含义是明确的:人一旦按照什么对我有用(即有益)、什么对我无用(即有害)的标准,来界定现实存在的动植物,下一步就要着手去“规划”它们了。德国的林业决策者们,按自己的意图去规划森林里自然生长的树木,结果把森林变成了军团。“最终人们甚至不必看到森林本身,只需在森林官员办公室的图表上就可以精确地‘读到’它们。”这则故事,与斯科特常常说的养蜂业改革的故事如出一辙,都以小见大,导入到对人类宏大的社会规划——即“国家的视角”——的总结和反思之中。
从《国家的视角》的角度出发,斯科特日后顺理成章地写出了自己版本的“人类简史”——一本名叫《作茧自缚: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》的著作,将它与尤瓦尔·赫拉利的《人类简史》或贾雷德·戴蒙德的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对读,会相当有意思。除了“国家化”这一条道路,人的发展还有其他的可能路径吗?那就要参看斯科特2014年的作品《六论自发性》(原题为“为无政府主义喝彩”)了,这本书讲了更多好故事,斯科特说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,他们是被支配、被统治的人,但他们凭无政府主义式的行为来强健自己的头脑和精神,用地方性的语言和思维,尝试在小范围内改善共同体的生活。斯科特提请我们考虑: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,是否一定要让“国家”有存在感,是否一定要把官僚制和等级制当成不可或缺的正常操作。
斯科特的书,一本比一本显得松弛。他的第三部作品《弱者的武器》,标志着他的著者身份从人类学者过渡为一名比较政治学学者。什么是“弱者的武器”?行动拖沓、假装糊涂、虚假顺从、小偷小摸、装傻卖呆、诽谤、纵火、破坏……它们通常不需要协调和计划;它们是个体的自助形式,避免直接对抗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;它们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力量。斯科特的这本书,被他心目中的偶像——人类学巨匠克利福德·吉尔茨誉为“圆融”之作;书中的一个谨慎的结论是:农奴、奴隶和贱民,用他们“朴素的想象力”,通过狂欢、仪式崇拜、玩笑等日常方式,颠覆他们在所处的社会秩序里的地位,打破酬劳的配置。
一个资质平平的农民
以农民研究起步的斯科特,自己也常年打理农场,他喜欢养羊,把一只小羊的出生,踢着腿蹦蹦跳跳的样子,看作世上最大的神奇。他自己作品的个人简介中也会加上“一个资质平平的农民”和“不成器的养蜂人”之类的提法,但中国的出版商,也许还包括译者,似乎总是不能领会他的幽默和性情,不能共情他对“讲真话”的迫切渴望。围绕饲牧的工作当然比写书有意思,打理农业的事,使他频频进入人类的心理和文化中那些令他最感兴趣的区域里。
英语中有很多俗语、成语是源于农牧业的。例如“a long row to hoe”,意思是有一大堆事情难于处理。斯科特说过,他的一个朋友在给豌豆锄草时,自言自语了一句“What a long row to hoe”(有好长的一片草要锄呀),然后就意识到,自己不经意说出了那句成语的本义。斯科特自己,看到羊儿吃光了草皮这里的草,就把脑袋伸过栅栏,去觊觎那边的草时,也会会心一笑,想到英语里的那句“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”(篱笆那边的草更绿)。
他的体会是:亲身做了农民后,才不仅知道农民有多么辛苦和脆弱,也许会被一片打来的涟漪淹没,更对自己所用的语言源于何处有了切身的体会。学者就得用学者的方式来滋养他的趣味,来寻求松弛。看斯科特说的这些趣事股市配资,我也想起曾看过的一则故事:某地兵营一天夜里着火,大家出来七手八脚把火扑灭了,兵营的领导照例要发表一通总结,只见他站到前列,慷慨陈词:“大家干得很好,很好,这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!”
发布于:上海市